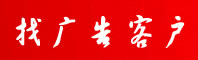- [经营]浅析商业动画的艺术性与商业性
- [经营]谈传统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技术
- [经营]三维动画技术在固体物理学教学
- [经营]三维动画技术与三维虚拟技术探
- [杂谈]媒体创新与渠道变革
- [杂谈]媒体创新与渠道变革
- [经营]中国未来10年的新媒体趋势与
- [杂谈]新媒体这么屌,酒商你知道吗?
- [杂谈]三招让媒体站着把钱挣了!
- [经营]纸媒不老 变革前行
- [杂谈]论新媒体时代电视的媒体价值
- [杂谈]广告主电视广告预算逐渐向在线
- [经营]新媒体太热:或是另一个危机或
- [经营]纸媒的时与命
- [杂谈]药品专题广告停播后—城市广电
- [经营]对城市电视台几种经营管理模式
- [经营]城市广电台如何实施经营创新系
- [杂谈]传统纸媒转型之路
- [杂谈]报纸广告经营策略探讨
- [杂谈]纸媒风光不再,媒体人出路何在
2006年春,湖南卫视正式宣告新一轮的《超级女声》再次启动,这不免让人重新想起去年的那场全民狂欢,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争议。确实,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档节目能凭借15万人的参与、数亿人的关注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注定它会在中国电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与《超级女声》相伴的则是中性美,它成为2005年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时尚,在今天的大街小巷,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的身影。那么,究竟什么是中性时尚?它从何而来?其本质又是什么?与媒体有何关联?这一切自然成了文化研究学者想要破解的迷局。
一、作为媒介事件的《
撇开外界加诸其身上的诸如庸俗、民主等评判不说,单纯从一档电视节目来说,《超级女声》的成功是毋庸讳言的:首先是收视率——这是衡量电视节目成功与否最直接而客观的标准,据初步估计,在全国范围内收看前5场总决选的观众总量达到1.95亿人。其中总决选6进5的直播收视份额更高达19.45%,同时段排名列全国所有卫星频道第一名。这也是地方频道叫板央视最强势的一次。其次,从参与人数来说,其15万人的广泛参与度,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是盛况空前的。最后,《超级女声》通过平民造星运动产生的几位“super star”迅速窜红,其影响力直逼在娱乐圈闯荡多年的大腕级人物。冠军李宇春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超级女声》的成功无疑是一桩媒介事件。所谓媒介事件,西方传播学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指的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在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在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的栏目或节目被不同的受众群体所选择、所分割,大众传播趋向“小众传播”的情况下,“媒介事件”却始终表现出它对空间、时间以及对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的“征服”。它是一个为几亿、几十亿人关注并为之激动的“神圣的日子”;是国家级或世界级的“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群体情感的一种宣泄。这样,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超级女声》都显然完美的成为了一个媒介事件的范例。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两位学者指出,媒介事件的成功需要提前的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而观众则是被“邀请”来参加仪式的。《超级女声》作为一桩媒介事件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精良的策划和无所不在的广告宣传。早在推出之前,其广告便开始在电视、网络上崭露头角,并且它在借鉴《美国偶像》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策划:一个主题“想唱就唱”,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对参赛选手没有硬性规定,免费报名,只要是想唱歌爱唱歌的女性即可;短信投票的优胜者产生方式,与观众进行密切的互动……所有这些以及后来异常激烈的比赛实况都使得《超级女声》成为了一种“仪式”——它使得庞大的观众群体为之激动,它扣人心弦、令人神往。它以一种收视状态为表征,在此状态下,人们相互转告必须收看,必须把别的一切搁在一边。上星卫视对全国范围的覆盖更是突出了收视的价值,乃至必要性,它使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集体而不是个体的庆典。
在这场由媒介主导的庆典中,“竞赛”、“加冕”、“狂欢”构成了此次“媒介事件”的主要叙事形式。“竞赛”是有规则的冠军之战,它让势均力敌的个体或团体相互对抗并按严格的规则进行竞争。在《超级女声》中,规则就是你的歌声必须征服电视机前的观众,让他们掏出手机来为你投票。所有的比赛都无非是围绕着分赛区冠军乃是全国总冠军而来。在每场比赛后,失败者黯然离场,成功晋级的选手们则在主持人及现场观众、FANS狂乱的欢呼声中甚至是煽情的泪水中让电视为她们“加冕”。电视认真地讲述了它的象征意义,同时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而在整个庆典的过程中,“狂欢”一直是其最好的界定。数量庞大的观众群体为几个原本普通的邻家女孩集体癫狂,种种骇人听闻的拉票行为不时见诸报端,而非专业的比赛规则和唱功平平的李宇春的最终胜出都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彻底嘲弄。
在这场平民化的狂欢中,大众的情感得到宣泄,而传统则被颠覆,新的时尚开始流行,譬如中性美。严格来说,以中性装束为美古已有之,然而当《超级女声》中众多中性打扮的少女崭露头角,再加上大众媒介有意无意的渲染,中性美开始逐渐流行。而当传统美女叶一茜被“中性帮”中人气平平的黄雅莉轻松拿下,当李宇春、周笔畅这两个中性少女最终问鼎冠、亚军,电视媒介以话语建构者的权威身份将中性美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时尚彻底的推向了大众。大众的审美标准在媒介无孔不入的侵蚀下开始显山露水的异化,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也迅速从观念层面深入到实践层面,留着李宇春式的发型、戴着周笔畅式眼镜的中性装扮的身影开始充斥大街小巷——“白马公主”,俨然成了后超女时代的一大景观。然而,这种审美标准的改变到底能在多大意义上代表妇女解放,中性美的出现是否值得女性主义者为之额手称庆?我们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去探寻其本质。
二、白马公主:跨越性别鸿沟的时尚幻象
中性美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是与传统的审美标准相对立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在这样一种男权社会里,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性与女性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男人被冠以“阳刚、坚强、理性”等诸多积极正面的形容词,而女人则与“阴柔、软弱、感性”等相比之下次等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女性则是附庸、屈从于男性的。于是,对女性的审美标准自然是男权话语建构的产物。何谓美女自然也是由男人说了算:不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至少也得是“温柔婉约,婀娜多姿,清纯脱俗或妖娆妩媚”。男人以绝对的权威勾勒出社会中妇女应具备的形象,而广大妇女则以此为目标去为“悦己者容”。在这样一种男权的强大优势下,男性是审美主体,女性则一直处于“被看”的地位。
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则带给人们一种不同与往常的审美观——中性美,“白马公主”开始流行。在《超级女声》炙手可热的几个名字里,无论是从不穿裙子、表情冷酷的李宇春,还是永远都带黑框眼镜、一身中性装束的周笔畅,以及假小子样的黄雅莉,她们都不具有男性话语所定义的女性的“美丽身体”。而根据调查,支持李宇春、周笔畅问鼎冠亚军的数以百万计的歌迷多是女性,她们按照自己对美的定义选出了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中性美女形象,而这种中性美也在媒介不遗余力的推崇下迅速使“白马公主”成为时尚。由此观之,“白马公主”的成功似乎颠覆了以往由男人话语建构的美女标准,女性俨然成为了审美主体,而不再象从前那样受男性文化的控制,女性不再只是单纯的审美对象。一批社会学家、女性主义学者纷纷认为《超级女声》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性审美观的革命,并将其视为女性解放的重大进步而欢欣鼓舞。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上。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虽然女性主义者直至今日依然在苦苦奋斗,然而,女性的经济地位却并无多大改变。虽然现代女性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但无庸讳言,男性依然是这个世界的核心。社会结构安排也从社会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有数据表明,越往上层,女性越少,权威角色依然被男性垄断。这并不是说,女性的素质就低于男性,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求职过程中,“刻板印象”以及对女性的各种偏见都大大限制了女性的天空。由此可见,到如今女性依然没有获得足够的经济与政治待遇,从而也就没有力量来与男性抗衡,女性依然处于屈从地位。
而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低下也必然导致女性文化地位的低下,从而丧失了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与之相对应的是,男性话语霸权仍活跃在这些领域。用福柯的话来说,“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话语权力的失衡,是性别统治和性别压迫的重要原因。而在大众娱乐领域,男性话语权力占统治地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通常处于被观看的位置,并由男性来确立有关女性形象的审美标准。《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商业运作的娱乐节目,以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为宗旨。而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以女性为看点的产品自然好卖过以男性为看点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是《超级女声》而不是《超级男声》红遍大江南北的原因所在。正如美国学者所评判的那样:“大多数美国电影是由男人和为男人拍摄的,而女人则变成了一种景观。”同样,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女性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看”与“被看”成了权力实践的一部分,而女性的“被看”正是被这种权力结构所先定的。不论其是作为传统女性美而“被看”还是作为中性美而“被看”,如果“被看”的命运并无改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奢谈女性的解放?由此可见,《超级女声》所带给我们的中性美与“白马公主”不过是一幅“看起来很美”的印象派作品。
进一步来说,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产生的,绝大多数女性,包括许多女性传播者,因为各种原因,明显“缺席”于女权主义,她们没有大规模女权运动的斗争经历,而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被赐予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正是因为如此,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然而,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传播者利用它所把持的话语权给大众建构了一座虚拟的“镜像之城”,在这个“镜城”中,女性被折射出的形象虽然华美却不真实。正如《超级女声》推出了几个中性美女,大众媒介就想让女性在政治上无法获得的解放在文化中假想式的获得。但假想毕竟是假想,妇女解放是无法从媒介所推销的几个流行概念中实现的。在这场所谓的审美革命中,“白马公主”不过是媒体在狂欢中为我们所制造的一场跨越性别鸿沟的时尚幻象。
三、温柔一刀:时尚面纱下的消费魔咒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去除掉了加诸《超级女声》之上并不实际的影响与意义,将中性美与“白马公主”回归为大众媒介制造的一场时尚。而众所周知,时尚的本质在于变,从古到今,一个个时尚不断替代了前面的时尚。时尚永远是变化多端的,而正是这种善变才使得时尚魅力四射,追赶时尚的人们则不辞劳苦的紧随其后,亦步亦趋。时尚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总是或多或少的影响其所在的社会,正如当年楚王好细腰,宫女则多饿死;而到唐明皇宠爱杨贵妃时,民间又开始流行“丰乳肥臀”。可见,中性美作为审美标准上的一场时尚革命,其生命周期注定是短暂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必将对社会实施其应有的影响力。
单从现象上来看,中性美的影响在于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白马公主”,而在这幅时尚面纱之下的,则是一股波及全国的“中性消费”狂潮:李宇春式的发型开始在各大理发店批量“生产”,周笔畅式的眼镜在各大眼镜店卖得脱销,其他中性的服装和饰品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这种纯粹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炫耀需求和攀比需求),有时纯粹是为了满足占有欲的消费不免走到了消费主义的一脉。消费主义占有或消费物质商品,有时固然是为了满足其物质上的需求,但更多的是一种主观需求,符号价值远远超过使用价值。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或消费永不满足。在这场“中性美”的时尚中,《超级女声》以解放女性传统审美观的名义刺激了新的一轮消费。大众对中性服饰、发型、眼镜等等中性饰物的消费已不再为了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而是把商品看作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身份或地位的象征,把物质消费看作是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一种形式,看作是生活质量和幸福人生的象征。只要是中性打扮,那么就代表着时尚,代表着永不落伍。可见,消费主义在打造中性时尚潮流时,把物质形式的商品消费,代之以符号意义的完成和满足,以诱导大众进行“非理性的消费主义狂欢”。
这种非理性的消费体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中性打扮,一些人追赶时尚反而弄巧成拙,东施效颦。那么,谁是这场时尚背后最大的赢家?我们可以看到,且不论《超级女声》最大的东道主——湖南卫视,单看它的另外两家合作单位:成都经济频道与南京电视台18频道,《超级女声》在这两家播出时,带动其收视率分别上涨了72%和25%,而份额则分别提升了39%和43%,收视率及份额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广告收入的增加,勿庸置疑,参与进来的媒体攫取了极其可观的效益。而《超级女声》的合作商蒙牛乳业也不甘示弱,其产品“蒙牛酸酸乳”的销售额从7亿一举跃升到了25亿,成为乳酸饮料的第一品牌。而李宇春、周笔畅们的收益自然也不小,比赛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是各个广告商们争先恐后邀请其担任形象代言人,据说酬金都是天价。当然,那些借力“中性”时尚而大卖“中性”产品的商家们,也没有闲着,自然是狠狠赚了一笔。由此看来,媒体、投资商、各路商家以及明星们才是这场狂欢盛宴中蛋糕的最大分割者。
在中性时尚被我们还原为以解放的名义刺激新一轮消费之后,《超级女声》的民主神话也就破灭了。《超级女声》声称比赛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观众手中,观众可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选手的去留以及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产生了一种草根民主。然而,身份等级秩序并不会象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比赛中已经消失。其实际情况可能是,人们借以确立身份差异的手段与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超级女声》短信投票的收费标准是一元一条,每个人可以给自己支持的选手投15票。每场比赛后,投票全部清零,而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投票累计。换言之,观众必须不停地为自己喜爱的选手发送短信支持,而所花去的费用可能是一大笔,显然,这并不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的,下岗的民众难道会参加这种游戏吗?于是,投票方式所收取的费用以一种隐而不露的方式将大多数出不起短信费的民众拒之于“民主”的门外。再者,在对中性时尚的消费中,所谓的时尚也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中性服饰因其流行而要价更高,中性时尚还是只属于富人,下层消费者根本无法企望。由此可见,经济实力与消费方式这时已经与身份认同紧紧的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身份区隔的作用,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不平等关系。这样看来,《超级女声》并没有体现所谓政治上的民主及解放,反之,它更能代表的是大众文化与市场的共谋。
由此可见,时尚的制造者总是时尚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时尚的恶果总是被转嫁到消费者或者社会大众身上。事实上,不管是昔日的皇家还是今日的大众媒介,单一的话语建构总是产生单一的审美标准或曰时尚,从而会导致一系列消极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国饿死的宫女跟现代女性东施效颦的中性装束同样让人同情。审美标准的单一是本质主义的体现,本质主义表现在性别论上,则是认为两性及其特征是截然分开的,女性特征被绝对的归纳为温柔的、母性的,而男性特征则被归纳为勇猛的、独立的。而反映在审美领域,一言以蔽之,则是女人就应该是女人那样,而男人就应该是男人那样。表面上看,中性美的出现解构了本质主义在审美上的二元对立,对女性有积极意义。但是,单一的中性美时尚又将女性推入了另外一个桎梏其个性的泥沼,它无非是以一个新的标准来取代老的标准。其实,一个现代社会其核心应该是反本质主义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无论是审美标准还是其他价值观念,多元并存可能更优越于唯一标准的单调乏味。
2005年的《超级女声》早已落下帷幕,亿万观众也从电视仪式中回过味来,重归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但它留给我们的中性时尚却还在继续,并影响着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女性美的看法。对于这次电视所释放的媒体神话,也许真如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时尚还能持续多久,这个神话还将演绎到何时,这依然是一个悬念。更让人值得玩味的是,在《超级女声》2005年引爆了中性时尚后,2006年它又拿什么来奉献给广大观众呢?
来源:媒中媒 作者:蔡骐 谢湘莉